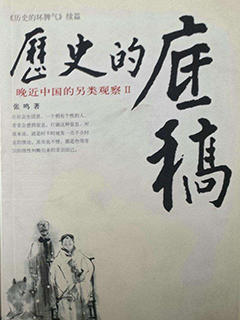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十五章
2018-5-26 06:02
從來的頑固派都是這樣,幹事不行,搗亂有術。他們看準了西太後對保皇黨和革命黨兩頭害怕的心病,就是從這兩點集中下蛆,非說應試者不是康黨就是亂黨,鬧得風聲鶴唳,把個開初頗有聲勢的經濟特科考試,攪得奄 奄壹息。特科考試分初試、復試兩場進行,1903年7月9日初試的時候,由於謠言四起,流短飛長,不免人心惶惶,原來得到保奏的370多人中,來考試的只剩下了190多個,有將近壹半的人不來應試了。幸好,由於初試有張之 洞領銜主持,張畢竟是個務實派的健將、明白人,有他當家,考試還算正常。試題為壹論,壹策,論題為“大戴禮保保其身體、傅傅之德義、師導之教訓與近世各國學校體育、德育、智育同義論”(斷句為筆者加,大戴禮是 大戴禮記的意思,即漢代戴德所編輯整理的禮記),策論題為“漢武帝造白金為幣、分為三品、當錢多少各有定直、其後白金漸賤、制亦屢更、竟未通行、宜用何術整齊之策”,雖然有西學中源的濫調,多少還有點西方的影 響。考試過程的選拔也還公允,懂西學而且有見識的人,真的被選拔出來了。可是初試發榜之日,風波再起,原因是中試的頭兩名,分別是梁士詒和楊度。這倆人在後來的歷史中聲名赫赫,可是在當時卻沒多少人了解他們的 底細,市面上哄傳這兩人跟保皇黨和革命黨有關系,或者幹脆就是康黨和亂黨。當然,楊度也許不算冤枉,他的確跟革命黨和保皇黨人都有那麽點瓜葛,但他個人卻兩邊的任何組織都沒有參加,事實上也算不得黨人。而梁士 詒,則比竇娥還冤,他被人找上門,竟然僅僅由於他的名字和籍貫。首先,他是廣東人,跟康、梁是同鄉,這在頑固派大臣眼裏,已經有了壹份嫌疑了,加上他的名字梁士詒,姓跟梁啟超同,名的尾,跟康有為的字祖詒同, 據說瞿鴻ND324直接向西太後匯報,居然把他說成是梁啟超的弟弟,而且名字“梁頭康尾,其人可知”。
【未完待續】
12008字節
神經過敏的“經濟特科”考試(2)
中國的事就是這樣,不管事情多麽荒唐,只要最高領導人起了疑,假的也變真的了,荒唐難免演變成荒謬,不由得人不害怕。所以,最後復試的時候,更多的人不見了,楊度和梁士詒自然無法繼續考下去,楊據說還逃到 了日本。而且主考也由原來的八人,變成了四人,張之洞的領導權也被剝奪了,昏庸的滿人親貴榮慶當了頭。考題也變了,同樣是論、策兩題,題目中不見了西方的蹤影,論題為“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”,從原來的打 著禮記的名義討論西方學校制度,變成了歌頌自己的制度(周禮)的完備。策論題為“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、則國用給、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泄、其道何由策”(桓寬,即著《鐵鹽論》的那位仁兄),也帶上了 明顯的保守色彩(說外國貨物輸入是異物)。考試最終只取了27人,而且,取了之後,並不給什麽好的出路,其中不是進士的,也沒有像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科中式者那樣,賞給進士出身,僅僅發到地方以知縣候補。在晚清捐 班泛濫的情景下,壹介區區候補知縣,跟販夫走卒沒有多少區別,害得考第二名的張壹ND252,不得不跑到袁世凱幕中做幕僚討生活,壹丁點“榜眼”的神氣也沒有。就這樣,在外界看來屬於清朝新政序幕的第壹炮,無聲 無息地啞掉了。
其實,就當時而言,跟1860年代,洋務派跟倭仁等人就開辦同文館的爭論不同,此時頑固派的攪混水,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,已經不是主義之爭,而是權位之爭,利益之爭。他們之所以嫉恨經濟特科,其實只是為了把 自己的位置多保壹會兒,雖然未必擔心新人上來讓他們沒了飯碗,但惟恐務實派上臺,導致他們的失勢。他們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,也擔心務實派的大膽和貪黷,不僅使官場腐敗無可遏制,而且導致社會道德滑向深淵(這 種憂慮當然不無道理)。從更深壹層的意思上面說,很多人是從經濟特科這個小老鼠,看到了後面科舉改革的大木鍁,為了阻止這個大木鍁露頭出來,所以要從壹開始就將之妖魔化到亂黨和康黨的堆裏,嚇退對改革已經食指 大動的西太後。盡管甲午戰爭已經教訓了國人,盡管戊戌之後的倒退已經把國家推到了崩盤的邊緣,盡管多數士人其實內心深處也知道中國非改弦更張不可,但整個知識界的現狀,人們對接受新知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接受新知 能力的懷疑,導致了更多的人還是幻想著把原來的科舉多保留壹天是壹天,哪怕變革僅限於考試的內容。最好是能將變革推到後代身上,免得自己陷入舊知無以用,新知又無以生的尷尬境地。畢竟,處在那個轉型的時代,剛 剛過去的維新變法,被血腥鎮壓,士林的正氣,受到嚴重打壓之後尚未復原(事實上,不給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復原),多數人的因循心態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這種心態,恰是頑固派得以囂張的基礎,在轉型時期,不見得改 革者都有群眾擁護。
然而,歷史從來不會按照因循的人們所渴望的步調行進的。朝廷中有最後決定權的西太後,雖然戊戌政變的時候出於私心,壹時糊塗,鑄成大錯,但她從來就不是什麽頑固派,更不是頑固派首領,從某種意義上講,她倒 是跟務實派心有戚戚焉。頑固派的阻嚇戰術固然可以得逞於壹時,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這個強人老太婆。深諳官場內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後,很快就明白了圍繞經濟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風背後的奧秘,在現實和洋人的壓力下, 屁股逐漸坐在了務實派壹邊,清廷的新政,還是按計劃拉開了大幕。只是,由於經濟特科的事件,原本很稀缺的西學人才,本可以通過經濟特科考試集中在中央政府,為即將到來的改革做準備,現在則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對立 面,就落到了地方實力派的囊中,進壹步強化了朝廷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。同時,事件激化了頑固和務實兩派的政爭烈度,導致科舉改革,也就是選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,朝著更加激進的方向進行,掌握主動權的務實派 ,要壹下子端掉頑固派的基礎,所以,廢科舉(推倒重來),而不是廢八股(內容改良,這恰是戊戌變法的做法),成為變革的主調。原來設計的從開經濟特科,再到把特科變成常科的改革思路,從此胎死腹中。顯然,從後 面的結果看,廢科舉這種突變式的變革所引發的社會震蕩,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,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。
以清末歷史觀之,中國的變革,是不可避免的,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,中國已經被拉入了以西方規則建構起來的世界體系之中。不過,是自己變,從自己的傳統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,還是引發內亂,走向混沌,卻不見得 有壹定的規律。歷史從來不見得按進化的步伐行進,明天未必會比今天好,但是有壹點是肯定的,就是在轉折的關頭,為政者保守的政策、開倒車之舉,往往是激進改革甚至內亂的根苗。如果主政者能少壹些神經過敏,多壹 些大度寬容,則事情多少要好辦壹點。
【未完待續】
12008字節
神經過敏的“經濟特科”考試(2)
中國的事就是這樣,不管事情多麽荒唐,只要最高領導人起了疑,假的也變真的了,荒唐難免演變成荒謬,不由得人不害怕。所以,最後復試的時候,更多的人不見了,楊度和梁士詒自然無法繼續考下去,楊據說還逃到 了日本。而且主考也由原來的八人,變成了四人,張之洞的領導權也被剝奪了,昏庸的滿人親貴榮慶當了頭。考題也變了,同樣是論、策兩題,題目中不見了西方的蹤影,論題為“周禮農工商諸政各有專官論”,從原來的打 著禮記的名義討論西方學校制度,變成了歌頌自己的制度(周禮)的完備。策論題為“桓寬言外國之物內流而利不外泄、則國用給、今欲異物內流而利不外泄、其道何由策”(桓寬,即著《鐵鹽論》的那位仁兄),也帶上了 明顯的保守色彩(說外國貨物輸入是異物)。考試最終只取了27人,而且,取了之後,並不給什麽好的出路,其中不是進士的,也沒有像康乾時的博學鴻詞科中式者那樣,賞給進士出身,僅僅發到地方以知縣候補。在晚清捐 班泛濫的情景下,壹介區區候補知縣,跟販夫走卒沒有多少區別,害得考第二名的張壹ND252,不得不跑到袁世凱幕中做幕僚討生活,壹丁點“榜眼”的神氣也沒有。就這樣,在外界看來屬於清朝新政序幕的第壹炮,無聲 無息地啞掉了。
其實,就當時而言,跟1860年代,洋務派跟倭仁等人就開辦同文館的爭論不同,此時頑固派的攪混水,對他們中的很多人來說,已經不是主義之爭,而是權位之爭,利益之爭。他們之所以嫉恨經濟特科,其實只是為了把 自己的位置多保壹會兒,雖然未必擔心新人上來讓他們沒了飯碗,但惟恐務實派上臺,導致他們的失勢。他們中的某些以清流自居者,也擔心務實派的大膽和貪黷,不僅使官場腐敗無可遏制,而且導致社會道德滑向深淵(這 種憂慮當然不無道理)。從更深壹層的意思上面說,很多人是從經濟特科這個小老鼠,看到了後面科舉改革的大木鍁,為了阻止這個大木鍁露頭出來,所以要從壹開始就將之妖魔化到亂黨和康黨的堆裏,嚇退對改革已經食指 大動的西太後。盡管甲午戰爭已經教訓了國人,盡管戊戌之後的倒退已經把國家推到了崩盤的邊緣,盡管多數士人其實內心深處也知道中國非改弦更張不可,但整個知識界的現狀,人們對接受新知的恐懼以及對自身接受新知 能力的懷疑,導致了更多的人還是幻想著把原來的科舉多保留壹天是壹天,哪怕變革僅限於考試的內容。最好是能將變革推到後代身上,免得自己陷入舊知無以用,新知又無以生的尷尬境地。畢竟,處在那個轉型的時代,剛 剛過去的維新變法,被血腥鎮壓,士林的正氣,受到嚴重打壓之後尚未復原(事實上,不給戊戌平反不可能真正復原),多數人的因循心態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這種心態,恰是頑固派得以囂張的基礎,在轉型時期,不見得改 革者都有群眾擁護。
然而,歷史從來不會按照因循的人們所渴望的步調行進的。朝廷中有最後決定權的西太後,雖然戊戌政變的時候出於私心,壹時糊塗,鑄成大錯,但她從來就不是什麽頑固派,更不是頑固派首領,從某種意義上講,她倒 是跟務實派心有戚戚焉。頑固派的阻嚇戰術固然可以得逞於壹時,但不可能真正蒙得了這個強人老太婆。深諳官場內幕和人情世故的西太後,很快就明白了圍繞經濟特科刮起的政治旋風背後的奧秘,在現實和洋人的壓力下, 屁股逐漸坐在了務實派壹邊,清廷的新政,還是按計劃拉開了大幕。只是,由於經濟特科的事件,原本很稀缺的西學人才,本可以通過經濟特科考試集中在中央政府,為即將到來的改革做準備,現在則不是推到了政府的對立 面,就落到了地方實力派的囊中,進壹步強化了朝廷內輕外重的政治格局。同時,事件激化了頑固和務實兩派的政爭烈度,導致科舉改革,也就是選官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,朝著更加激進的方向進行,掌握主動權的務實派 ,要壹下子端掉頑固派的基礎,所以,廢科舉(推倒重來),而不是廢八股(內容改良,這恰是戊戌變法的做法),成為變革的主調。原來設計的從開經濟特科,再到把特科變成常科的改革思路,從此胎死腹中。顯然,從後 面的結果看,廢科舉這種突變式的變革所引發的社會震蕩,以及由此產生的不良後果,大大超出了改革者的預期。
以清末歷史觀之,中國的變革,是不可避免的,因為從鴉片戰爭以來,中國已經被拉入了以西方規則建構起來的世界體系之中。不過,是自己變,從自己的傳統秩序走向人家的秩序,還是引發內亂,走向混沌,卻不見得 有壹定的規律。歷史從來不見得按進化的步伐行進,明天未必會比今天好,但是有壹點是肯定的,就是在轉折的關頭,為政者保守的政策、開倒車之舉,往往是激進改革甚至內亂的根苗。如果主政者能少壹些神經過敏,多壹 些大度寬容,則事情多少要好辦壹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