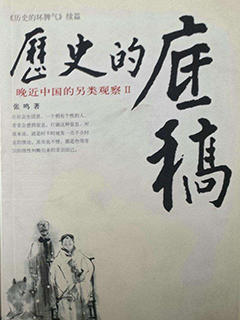- [ 免費 ] 第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章
- [ 免費 ] 第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五章
- [ 免費 ] 第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七章
- [ 免費 ] 第八章
- [ 免費 ] 第九章
- [ 免費 ] 第十章
- [ 免費 ] 第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二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三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四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五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六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七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八章
- [ 免費 ] 第三十九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壹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二章
- [ 免費 ] 第四十三章
杏書首頁 我的書架 A-AA+ 去發書評 收藏 書簽 手機
简
第二十三章
2018-5-26 06:02
歷史似乎在借助“義和團藥方”告訴我們,凡是大規模的群體性恐慌,往往與當局有意無意地控制信息有關。事情就是這樣,越是擔心真相的暴露會引發人心的騷動,就越是容易引起人們的不安。當正式的渠道閉塞的時 候,人們對於各種非正式渠道就格外地依賴,從而導致小道消息乃至訛言被激活,群體在傳播和接受訛言的時候情緒相互感染,恐慌由此產生而且升級,直至出現危機。更加可怕的是,群體性恐慌所引發人們的緊張,使人們 會自動地尋求消解之道,緊張的情緒要有地方宣泄,不滿積聚要尋找替罪羊。這時候人們往往趨向於“做點什麽”,有點火星,有人刺激,就完全可能像潰堤壹樣形成騷亂,更不用說有人有意組織策劃了。
雖然,信息控制是傳統政治治理術的組成部分,但是某些聰明的統治者也知道,什麽時候能瞞,什麽時候不能瞞。在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波及每個人的時候,信息公開往往是化解危機的不二法門。因為公開的信息可以讓 人們知道如何規避危險,繞道而行,而反其道而行,則很容易使自己成為人們情緒激動後果的承受者。
義和團藥方的再現江湖告訴我們,人們在情形曖昧的危機時刻,其心境、情緒和行為大體上是相近的。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,正在流傳的藥方中有義和團的藥方,甚至人們可能並不真的相信這些中藥和藥方,可以治療今 日的非典型性肺炎。它的出現,不過是壹種人們在恐慌的時刻想要做點什麽的征兆。
時間雖然過了百多年,在觸及到人類最本原層面的時候,人的變化其實並不大。
廢科舉: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(1)
2005年是科舉廢除100周年。100年前,壹項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,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、袁世凱、岑春煊、端方等人壹攛掇,幾年前壹手埋葬了戊戌變法、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後下了壹紙詔書,就這麽完了。順手 翻了壹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、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,1905這年,關於廢科舉,居然壹字未提。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,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哇國裏,知識界看起來已經帖然接受了這個在後人看來幾 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。這個被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壹的科舉制,居然完結得這麽無聲無嗅,波瀾不驚,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,而且讓當時有點了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,驚奇之余,未免有點盲目樂觀,泰 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說:既然“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制度,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改革”(《清末民初政情內幕》)。
莫理循沒有明白,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制度變革,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,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。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,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,也斷不會如此迅速 ,更不會如此地朝野壹致。
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,只要國家出了問題,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,還是軍事上、制度上,甚至幹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裏有了麻煩,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,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頭上,打在士風或者學風上, 而最終又都反映在選舉(官吏選拔)上。自從秦漢創制以來,這種局面就形成了。選舉制度的幾次重大改革,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,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,以及中間小的變革,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,科舉考試內容 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等,無壹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。大抵自秦漢以來,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管理帝國,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雇員,形成了實際上的“半公司”架構,無論是追求效 率還是講求穩定,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,官吏的素質和能力,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“人治”的重中之重。這樣壹來,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“綱”,每次出了問題,大家就指望“綱舉目張”,壹抓就靈。
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,中國在應變方面的成績不佳,選舉制度自然難逃板子。自明末以來對八股制藝的批判聲,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壹連串敗績,越來越高。當然,壹般說來,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 ,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制藝的牢籠之中,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,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,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。不過,跟以往不同的是,此時的批判,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, 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——西方的學校制度。西方的節節勝利,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,很具有說服力。事實上,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,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, 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,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。這裏,人們不僅聽到了“破”的呼聲,而且看到了“立”的榜樣,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。這意味著,在中國歷史上,選舉制度的變革,第壹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, 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。
然而,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,在事實上跟科舉制度並不對應,至少不完全對應。嚴格來講,我們的科舉主要是壹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,屬於選官制度,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,學校制度(官學)日 益和科舉緊密地聯系在了壹起,成為科舉制度事實上的附庸。在明清兩朝,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,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壹個臺階——進學成為生員(秀才)。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制度,因為它事實上什麽都不教。不過,由 於科舉創制的時候,引述古義(周禮所謂的學校制度)所造成的先天誤會,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,因此,那個時候的人們,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,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,從 壹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制度來類比科舉,壹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。
其實,盡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壹起的,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,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,到了晚清時節,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壹段可有可無的闌尾。雖說各個府、州、縣都有學校,房屋設備齊全,但這種學校基本上 是不開課的,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。進學的實際意義,除了獲得參加進壹步考試的資格外,主要是為了擁有壹種初等縉紳的身份,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,並得到民間的尊重,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,其實是私學(各種名目的私塾),真正的老師,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(盡管,在那個時代,人們壹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,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。 這是壹種人際關系的扭曲,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)。所以,實際上,西方學校制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系,而不是科舉制度。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壹詞的“廢科舉,興學堂”,按理應是“廢私塾,興學堂” 才是。雖然,廢科舉後,私塾也走向式微,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。
雖然,信息控制是傳統政治治理術的組成部分,但是某些聰明的統治者也知道,什麽時候能瞞,什麽時候不能瞞。在人們意識到危險可能波及每個人的時候,信息公開往往是化解危機的不二法門。因為公開的信息可以讓 人們知道如何規避危險,繞道而行,而反其道而行,則很容易使自己成為人們情緒激動後果的承受者。
義和團藥方的再現江湖告訴我們,人們在情形曖昧的危機時刻,其心境、情緒和行為大體上是相近的。也許沒有幾個人知道,正在流傳的藥方中有義和團的藥方,甚至人們可能並不真的相信這些中藥和藥方,可以治療今 日的非典型性肺炎。它的出現,不過是壹種人們在恐慌的時刻想要做點什麽的征兆。
時間雖然過了百多年,在觸及到人類最本原層面的時候,人的變化其實並不大。
廢科舉: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(1)
2005年是科舉廢除100周年。100年前,壹項存在了1400年的制度,經當時的重臣張之洞、袁世凱、岑春煊、端方等人壹攛掇,幾年前壹手埋葬了戊戌變法、被人視為頑固派首領的西太後下了壹紙詔書,就這麽完了。順手 翻了壹下當時也算是小名人、而且對時政頗為熱心的鄭孝胥的日記,1905這年,關於廢科舉,居然壹字未提。戊戌變法時廢八股引起的軒然大波,此時已經消失在了爪哇國裏,知識界看起來已經帖然接受了這個在後人看來幾 乎是翻天覆地的改變。這個被著名學者許倬雲稱之為中國文化三原色之壹的科舉制,居然完結得這麽無聲無嗅,波瀾不驚,不僅令今天的我們不解,而且讓當時有點了解中國的外國人看了,驚奇之余,未免有點盲目樂觀,泰 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居然由此推理說:既然“中國能夠不激起任何騷動便廢除了建立那麽久的科舉制度,中國就能實現無論多麽激烈的改革”(《清末民初政情內幕》)。
莫理循沒有明白,廢科舉這項看起來最具現代性的制度變革,雖然似乎表現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熱忱,其實背後卻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。如果沒有這種老套路,科舉即使不可避免地會被廢除,也斷不會如此迅速 ,更不會如此地朝野壹致。
古代的中國人在政治上有個習慣,只要國家出了問題,無論這個問題是出在經濟上,還是軍事上、制度上,甚至幹脆就是皇帝自己家裏有了麻煩,大家在找原因的時候,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頭上,打在士風或者學風上, 而最終又都反映在選舉(官吏選拔)上。自從秦漢創制以來,這種局面就形成了。選舉制度的幾次重大改革,比如從察舉到九品中正,從九品中正到科舉考試,以及中間小的變革,如察舉從四科到唯經義是舉,科舉考試內容 從詩賦變八股的標準化演進等等,無壹不是這種找原因然後大批判的結果。大抵自秦漢以來,皇帝必須依賴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管理帝國,大小官吏等於是皇帝開工資的雇員,形成了實際上的“半公司”架構,無論是追求效 率還是講求穩定,都只能落在官吏身上,官吏的素質和能力,成為後來我們所謂的“人治”的重中之重。這樣壹來,選舉就成了王朝政治的“綱”,每次出了問題,大家就指望“綱舉目張”,壹抓就靈。
晚清面臨千年未有之變局,中國在應變方面的成績不佳,選舉制度自然難逃板子。自明末以來對八股制藝的批判聲,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壹連串敗績,越來越高。當然,壹般說來,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 ,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制藝的牢籠之中,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,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,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。不過,跟以往不同的是,此時的批判,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, 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——西方的學校制度。西方的節節勝利,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,很具有說服力。事實上,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,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, 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,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。這裏,人們不僅聽到了“破”的呼聲,而且看到了“立”的榜樣,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。這意味著,在中國歷史上,選舉制度的變革,第壹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, 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。
然而,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,在事實上跟科舉制度並不對應,至少不完全對應。嚴格來講,我們的科舉主要是壹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制度,屬於選官制度,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,學校制度(官學)日 益和科舉緊密地聯系在了壹起,成為科舉制度事實上的附庸。在明清兩朝,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,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壹個臺階——進學成為生員(秀才)。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制度,因為它事實上什麽都不教。不過,由 於科舉創制的時候,引述古義(周禮所謂的學校制度)所造成的先天誤會,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,因此,那個時候的人們,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,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,從 壹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制度來類比科舉,壹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。
其實,盡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壹起的,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,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,到了晚清時節,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壹段可有可無的闌尾。雖說各個府、州、縣都有學校,房屋設備齊全,但這種學校基本上 是不開課的,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。進學的實際意義,除了獲得參加進壹步考試的資格外,主要是為了擁有壹種初等縉紳的身份,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,並得到民間的尊重,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系 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,其實是私學(各種名目的私塾),真正的老師,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(盡管,在那個時代,人們壹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,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。 這是壹種人際關系的扭曲,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)。所以,實際上,西方學校制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系,而不是科舉制度。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壹詞的“廢科舉,興學堂”,按理應是“廢私塾,興學堂” 才是。雖然,廢科舉後,私塾也走向式微,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。